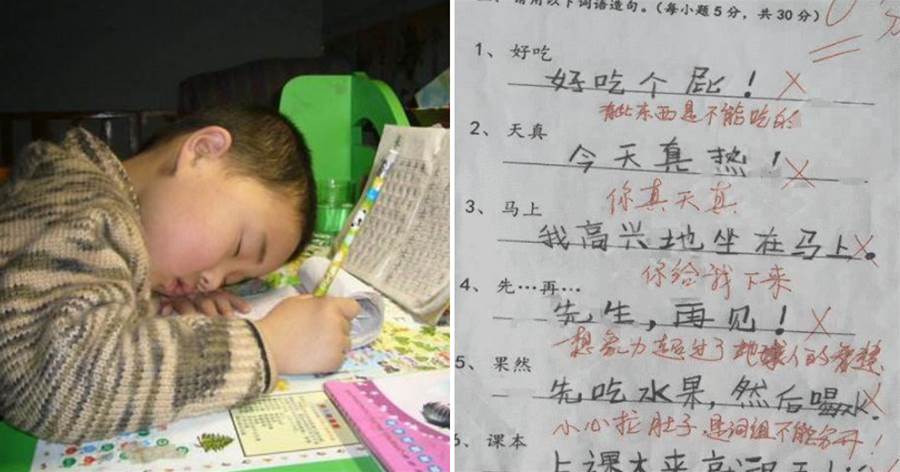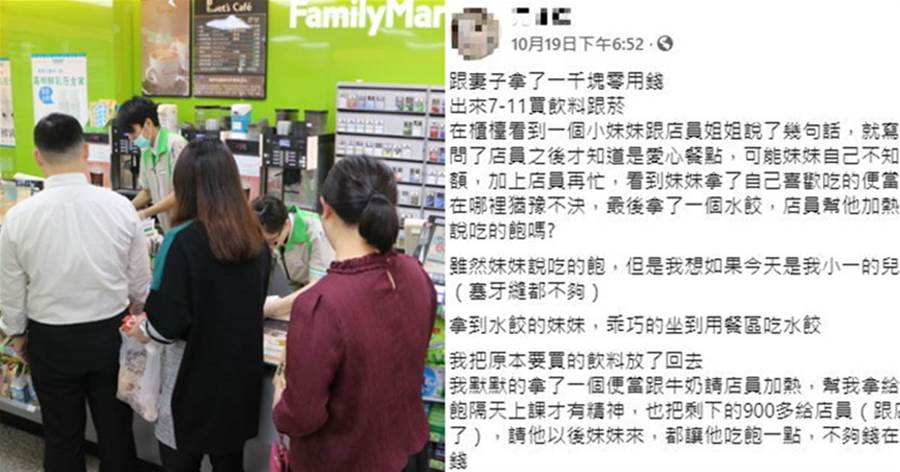劉娥是宋代皇后中情感經歷最為動人,宮廷生活最為曲折,輔政生涯最為盡心的奇女子,其動人的經歷令人唏噓不已。
劉娥出身非常卑微貧賤,在趙匡胤陳橋兵變后,父親劉通當上北宋的禁軍軍官,并出任了嘉州刺史一職,這時舉家遷往了四川。
當中有一部分頭銜是劉娥當上皇后之后才追加的。後來其父劉通在奉命北征太原的途中去世了,此時的劉娥剛出生不久,因其母龐氏在懷孕時夢見一輪明月入懷便給其取名劉娥。
童年時期的劉娥并沒有學會讀書寫字女工類的技能,只學會了擊鼗,并擅長說鼓詞,也就是這種技能為她後來遇見真宗埋下了伏筆。
十三歲那年,她嫁給了一個銀匠龔美。日子過得很清貧,龔美有了外出謀生的念頭,于是夫妻二人就到了京城。

這天趙恒在王府選姬,龔美以表哥的身份送劉娥來到了襄王府。趙恒和劉娥一見面便情投意合,如驚鴻一瞥。因為趙恒和劉娥有很多共同話題,劉娥越來越為趙恒所鐘情。
然而這件事情并沒有像想象中的那麼簡單,一方面,趙恒該如何處理劉娥的前夫銀匠龔美。
另一方面,在宋代宗室血統是非常被看重的,貴族和貧民之間的婚姻是不被看好的。
趙恒的乳母秦國夫人勸說無果后,便把這件事告到了太宗那里。宋太宗一聽勃然大怒,認為兒子不思進取,讓他把劉娥斥出王府。
趙恒當然不忍心舍棄佳人,于是將劉娥偷藏在張耆家中十五年,這十五年不但沒有拖垮他們的愛情,反而成就了一場傾世之戀。

至道三,宋太宗趙光義去世,太子趙恒上位,也就是後來的宋真宗。
宋真宗繼位后并沒有忘記與自己偷偷摸摸約會了十五年的劉娥,專程派人把她接到了宮中,封為「美人」。
此時的劉娥,已不再是當年蜀中擊鼓唱詞的歌女了,而是一個識書達理、通曉琴棋書畫的大家閨秀。藏在張耆家的這十幾年的時間里,為了排解對真宗的相思之苦,劉娥早已博覽群書,知曉禮儀,絲毫不遜于其他妃嬪。
真宗對劉娥可謂是一往情深,雖然此時的劉娥已三十六歲,但絲毫沒有受到冷落,反而被真宗寵愛有加。
劉娥被冊封為「美人」后,看見其他妃嬪的父母兄弟親戚都有在朝中的,自己卻是煢煢孑立,形影相吊,心里不免孤苦,于是,她便請求真宗賜前夫龔美姓劉。

在這件事情上,真宗表現出了男人的氣度,很干脆地答應了;當然,真宗也獲得了龔美忠心耿耿的回報。
此后的龔美改名叫作劉美,對宋真宗趙恒可以說是毫無二心,對真宗唯命是從。他在任職期間,從不攀附朝中權貴,也不依靠裙帶關系搞小集體。這樣一個老實忠厚的人,真宗自然對他也是相當信任。龔美雖出身卑賤,但并不趨炎附勢,做官以后也從不趾高氣揚,待人接物都很隨和,一直活到六十花甲才壽終。
真宗對劉美人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執著與寵愛。先前真宗奉父母之命娶了兩個妻子,一個是莒國夫人潘氏,當時趙恒還只是韓王;另一個郭氏,父親是宣徽南院使郭守文,時年十七歲受封為魯國夫人,后晉封為秦國夫人。
潘氏結婚六年后就去世了,沒有子嗣,而郭氏在真宗繼位兩月后被冊封為皇后。
郭皇后為人品性寬厚,溫柔賢惠,先后為真宗生下了三個孩子,但是這三個孩子卻紛紛夭折,從此郭皇后的身體由于悲傷過度而日漸消弱。
景德四年,悲傷成疾的郭皇后病薨,結束了晝思夜想的喪子之痛,享年三十一歲。

這件事也對真宗的打擊很大,因為先后一共五個兒子和兩任皇后都離開自己,真宗心里非常抑郁,但是有一件事真宗覺得現在是時候做了,那就是立劉娥為后。
但是劉娥出身卑微而且沒有子嗣,大臣們都不贊同,于是群臣紛紛力挺才人沈娘娘。
宋真宗到了而立之年,卻膝下無子,這使得他非常郁悶。
關于劉娥和李宸妃,一直有「貍貓換太子」的鬧劇之說,大意是說是在宋真宗的后宮中,劉德妃與李宸妃同時懷有身孕,李宸妃生下的皇子被劉德妃派人用一只剝皮貍貓換走,宋真宗以為她生一個怪物,便將她逐出皇宮,立劉娥生的兒子為皇儲。
據說「借腹」的計劃也是三人一起密謀的,劉娥真宗對李宸妃非常好,不存在什麼「貍貓換太子」之說。
後來,劉娥對李宸妃母子非常好。趙禎小時候身體不好,劉娥又忙著協助真宗料理朝政,便將照顧仁宗的職責交給楊淑妃代行,所以趙禎一直稱劉娥為「大娘娘」,稱楊淑妃為「小娘娘」。

劉娥當上皇后以后,真正成為了真宗的左膀右臂,不光是在生活上給予關心照顧,而且在朝政事務和后宮管理上也為真宗提供了不少幫助。
曾經幽居在張耆家的日子里讓劉娥變成了一個才華超群、知書達理的女子,無論朝中宮中都對這位劉皇后心悅誠服。
劉皇后的記憶力非常好,機警過人,對朝中大臣的關系了如指掌,所奏之事聽一遍就能記得清清楚楚。
在后宮里她小心謹慎,勤勞簡樸,從不鋪張,朝中宮中的事情都處理得非常妥當,既能遵照規矩又能給予關懷,真正地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,深得真宗信賴,嬪妃擁護,百官愛戴。

此時真宗趙恒已經離不開劉娥的輔助,每天奏折中所議的朝中大事都會告訴她。
而劉娥聰明機警,深諳處世之道,博聞強識,能把書上的道理和現實聯系起來,實時處理的得體,所以真宗一有什麼重大問題都會和劉娥商量一下,聽取她的建議。
真宗每天批閱奏章到深夜,劉娥三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在真宗身邊,不時給他提出建議。真宗每次出游巡幸各地都會帶著劉娥一同前往,二人一起走過了風雨兼程的三十年。
但是在儒家思想發展到極致的宋代,等級制度森嚴,宗族血統非常被看中,真宗雖然暗度陳倉地立了劉娥為皇后,但是朝中的老臣們對此事還是心存芥蒂的。

此時朝中分為兩大陣營:一是以宰相李迪、寇準為首的士大夫群體,一是以丁謂、錢惟演為首的朝中有勢力的重臣。
為了讓百官心服口服,身在高位的劉娥明白必須發展自己在朝中的勢力。
于是,她讓趙美娶了錢惟演的妹妹,籠絡錢惟演、丁謂一派。
而這兩派在朝中水火不容的關系,也促成了劉皇后朝中威信的確立。
天熙四年,真宗趙恒病重,太子趙禎年少,所有朝中事宜交給劉皇后處理,而劉皇后這時還是親丁謂派的,所以丁謂的勢力是炙手可熱的。

丁謂這個人當年是寇準提拔起來的,後來卻對寇準大肆排擠,恩將仇報,是個十足的小人。
而寇準則是剛正不阿、嫉惡如仇、有膽有識的人中豪杰,寇準心里明白,如今的朝政已經由劉皇后掌握,皇后是親丁謂一派的,自己要想有前途,還得依靠真宗,于是他便制造「天書」,籠絡真宗身邊的宦官周懷政。可是誰能料想到,這正是寇準、丁謂兩派矛盾爆發的導火線。
此時的太子趙禎只有十歲,太子監國就意味著必然是朝中的士大夫把持局面,這樣寇準就可以排擠出丁謂一派,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。
曾遭貶謫多年的寇準早已摩拳擦掌,他決定一不做二不休,立即向真宗提出讓太子監國、罷免丁謂職務的建議,誰知道病重的真宗竟然糊里糊涂地答應了。
寇準樂顛樂顛地回到家中,找來楊億喝酒,楊億素來敬重寇公的為人,便答應起草太子監國的詔書。

酒過三巡之后,抑郁已久的寇準覺得自己的春天即將到來,酒酣耳熱之際居然大聲嚷嚷地把自己的計劃和盤托出。
隔墻有耳,丁謂幾乎在寇準剛喝完酒就知道了這個消息,大為震驚之后便向真宗報告了這個情況,并大肆詆毀寇準,要求真宗對寇準嚴加查辦,病重的真宗居然也稀里糊涂地答應了。
于是豪放不羈的寇準又一次被罷相,相位落入李迪之手。這件事讓真宗很惱火,一是寇準急著讓太子監國,意欲自己掌權,二是寇準居然和真宗身邊的太監私交甚密。
周懷政是個膽大包天的人,看情況不妙,他跟平時關系不錯的楊崇勛、楊懷吉商量發動一場宮廷兵變,廢掉皇后劉娥、逼真宗禪位,并召回寇準擔任宰相。
誰知道這倆人出門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丁謂,丁謂大驚,趁夜間穿上便裝坐著婦人的馬車去聯系他的黨羽。

第二天,他們把這件事告訴了真宗,說寇準是幕后的主謀,并把寇準先前為了復相偽造「天書」的事情給揭發了。真宗龍顏大怒,想要誅殺寇準九族,李迪從中說了半天好話,真宗最后才決定貶他為相州知州,這時丁謂小人的心態又爆發了,他覺得相州不夠遠,便擅自改了圣旨,貶寇準為道州司馬。
宋真宗趙恒去世了,太子趙禎繼位。此時的劉娥已由皇后變成皇太后,由幕后走到台前,是大宋天下真正的決策者。就這樣,劉太后開始了長達十一年的聽政生涯。
掌權后的劉娥,首先做的是穩定人心,樹立威信。雖然真宗一道詔書給予了劉娥統御天下的名分,但是朝中的一些官員對劉太后還是不會心服口服。
首先是因為在前代屢屢出現因爭奪皇位而父子相殘、兄弟反目的前車之鑒,眾臣甚為擔心年僅十一歲的仁宗。
另一方面,劉娥出身卑微,士大夫階層中的一些人認為她不具有母儀天下的資格,對她還抱有成見。

所以劉娥做了三件事:一是加固與仁宗之間的關系,不允許任何人離間;二是培植自己在朝中的勢力,提高自己的地位。
劉娥做的第三件事情,就是罷黜丁謂,收回皇權。因為寇準士大夫一派一直對出身卑微的劉娥心存芥蒂,所以在劉娥正位后宮的時候,她籠絡的是丁謂一派的重臣。
現在劉太后成了真正的掌權者,丁謂一派當然是炙手可熱,飛揚跋扈。
這樣就形成一個局面:朝中事務丁謂管,軍政事務雷允恭管,直接架空了劉太后。丁謂這個人是個十足的小人,慣用卑鄙的伎倆,欺上瞞下,遞給劉娥的奏章都要經過他之手,對自己不利的統統不呈報,對百官同僚就拿太後來壓制不同意他意見的人,一手遮天。
喪心病狂的丁謂想要借劉太后之手置政敵寇準、李迪于死地,他令人把劉太后發下貶謫李迪、寇準的詔書纂改為誅殺他們的詔書,讓使者不得拿出詔書宣讀,直接逼李迪、寇準自盡,不過最后寇準還是識破丁謂的陰謀,逃過一劫。

丁謂此時有些得意忘形,根本不把年過半百的劉娥放在眼里,這使得劉太后很惱火,以前為了培植自己在朝中的勢力,只得籠絡丁謂一派,現在真宗下了詔書,劉太后已成為是統御天下的實際掌控者,丁謂這個人在朝中聲名狼藉,劉娥決定除去這枚釘子,加固皇權。
于是她找了一個機會:在雷允恭主持修建真宗的陵寢時,他擅自移動了地穴,而且倒霉的是他不偏不倚地移動到了一個泉眼上,這是風水中的「絕地」。
這件事他并沒有提前通知劉娥,劉娥知情后勃然大怒,立即下令將雷允恭拘捕查辦。
這時候,王曾便不失時機地向劉娥揭發丁謂,說他才是擅自移動皇陵的幕后指使者,他意欲破壞皇家風水、毀壞大宋江山,「包藏禍心,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絕地」。
王曾的這個舉動,恰巧符合劉娥的意圖,于是劉娥便將計就計,下旨罷黜了丁謂。
其實,這是劉娥早就想做的事情,丁謂這回真可謂多行不義必自斃。經過這三件事情,劉太后完成了對皇權的回收,加固了自己家族的地位,樹立了自己的威信,一心一意地開始輔佐仁宗開創北宋的中興時代。

劉娥聽政的十一年里,政通人和,百廢俱興,百官誠服,天下祥瑞。
十一年期間,無論在官場還是民間,始終有一些人認為劉娥的出身與她所擁有的權力不符,何況后妃干政,名不正言不順,包括范仲淹也曾進言阻止仁宗率百官為劉太后拜壽,對于劉娥的指責和攻訐也從未停止。隨著仁宗年齡的增長,要求劉太后還政于仁宗的呼聲也越來越高。
明道二年,劉娥冥冥之中感覺大限將至,便決定身著袞衣祭祀太廟,這在宋王朝以前是從來沒有的。
雖然遭到一部分官員反對,但最后劉太后還是身著天子袞衣、頭戴儀天冠在太廟完成了祭典初獻之禮,并在文德殿接受了百官獻給她的尊號:「應天齊圣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。」
過了一個月,劉娥在寶慈殿病逝。趙禎下詔將劉娥和李宸妃安葬在永定陵。

劉娥一生兢兢業業地陪伴在真宗身邊協助處理國家大事,在真宗死后,朝中兩派斗爭水火不容的情況下,受命于危難之際,完成了皇權的回歸,又十年如一日地教導自己的兒子,處理國家事務,處理后宮事務,完成了一個內無大憂,外無大患,百姓安居樂業,天下太平的北宋中興治世。
雖然劉娥在政治斗爭中為了確立自身地位、維護皇家權力而受到一些非議,但是就她為北宋一個朝代,她所立下的功勞而言,始終是瑕不掩瑜的。